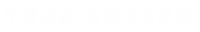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 , 当一门语言灭亡或即将灭亡的时候 , 它会经历简化的过程 。 这一点可以在满语等语言中看到 。 就比如说 , 在清初的时候 , 满语里光是“杯子”这个词就可能有十几种表达方式 , 像盅、盏之类的 。 但是 , 到了清朝末期 , 人们就只记得“杯子”这一种表达了 , 其余的全忘记了 。 我在现在社会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 , 至少在我孩子身上 。 他们只会说“杯子”(cup) , 没有人真得会说“圣餐杯”(chalice)或“高脚杯”(goblet)了 。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会说:“你不懂我们说话的方式 。 ” 但是十年之后 , 我们脑子里的这些词就会不复存在 。
您在澳大利亚从事亚洲以及中国研究以来的这几十年 , 学术界有什么变化吗?
康丹:对我来说 , 现在根本没有学术界可言 , 它已经不存在了 。 当然还是有几个非常出色的学者 , 但是很少很少 , 剩下的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中国 , 但这些所谓的“中国专家”几乎没人会说中文 , 更别说对当今的中国有任何了解 。 在学术界 , 你应该是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 与对文化、哲学、历史和艺术感兴趣的人一起思考问题 , 一起想出答案 , 不管他们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教授 。 以前的学术界 , 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理想村里似的 , 特别奇妙 。 但后来就分崩离析了 。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 , 或者如您所说的 , 不存在的学术环境中 , 您觉得年轻学者还能像您当年那样去研究灭亡或者濒危语言吗?
康丹:简短的回答是不能 , 原因有两点 。 首先 , 在2012年我退休时 , 政治正确已经占领了大学这片高地 。 如果我留在了麦考瑞或其他地方 , 我肯定是会被这些人攻击的 。 我离开的时机正合适 , 因为在我临退休之前 , 我工作所在的大学——麦考瑞的校长离开了 , 由一个美国人取而代之 。 新校长特别关注大学排名和出版产出之类的 。 从那以后 , 作为学术界的一员 , 你的价值就取决于你发表的文章数量了 , 最低要求是每年四篇 。 文章可不是说写就写的 , 更别提写书或者译作了 。
《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我不清楚霍克思和闵福德花了多久才把它译成英文 , 但肯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 我之前曾读过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译本 , 但是当我读霍克思翻译的《石头记》第一章时 , 每一个句子 , 我都拍案叫绝 。 真是登峰造极的境界 , 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句子的背后都是无尽的思考和付出 。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一样 , 这是在今天的环境中是无法取得的成就 。
您对今天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康丹:就像他们说的 , 你得“耕耘自己的园地”(此语出自伏尔泰的《老实人》 , 意思为创造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 。 你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这类人 。 有时候我会遇见让我刮目相看的青年学者 , 尽管在现在这样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下 , 他们仍然可以如此出众 , 如此博学 。 几年前我去罗马的时候 , 去了济慈墓 , 遇见一些美国学生 。 有一个美国女孩 , 她在济慈的墓前放声大哭 , 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 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 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女孩 , 就对济慈有如此深刻的欣赏与理解 。
本文图片
丹康先生与叶晓青女士
丹康教授著作目录 (由生前好友及学生整理)
1971: ‘Lo Chang-pei.’ Unpublished honours thesis,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契丹$契丹语版“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学习契丹小学生的读法
- 金国#同样是契丹人当丐帮帮主,为何乔峰被推翻,耶律齐获得一致认可?
- 萧氏@大辽传国九代,皇后皆出萧氏,契丹为何用汉姓,萧氏又从何而来?
- 李俨$曾经出使契丹的大诗人欧阳修,在诗句中记录了幽燕风土
- 耶律德光$曾经不可一世的契丹族,现如今属于哪个民族,其实只是换了称呼
- 血脉&最后的契丹——契丹民族血脉主要存在于现在的哪些民族当中
- 契丹@神秘消失的契丹族,究竟去了哪里!
- 专家们!契丹族为何突然消失?专家用DNA技术,在中国的偏僻地区找到
- 契丹族!契丹族为何突然消失 专家用DNA技术, 终于在中国一偏僻地区找到!
- |男子钓鱼捡到金牌,刻有契丹文竟是辽国文物,拒绝上交打成金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