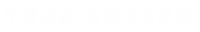雷切尔:那么你一定觉得为具有天赋付出代价理所当然了?
米沃什:是的 , 可能 。
雷切尔:在一首诗中你说你不会告诉嫉妒者这代价是什么 。 你是想让他们觉得这很容易吗?
米沃什:让他们这样想好了 。 在这个国家 , 某种程度上我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 因为这里有关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确定的观念 , 而我并不符合:我从来没有在精神诊疗所待过;我不使用毒品;也不酗酒(我喝 , 但有节制);所以我可能是不正常的 。
雷切尔:你是否认为一个人必须在情感上病态才能成为作家?
米沃什:不 。 我认为很多人都属于情感疾患 , 并且有很可怕的情感纠结 , 但是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 。 但是作家就不同了 , 这方面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泄露出来 , 于是人们都知道了 。
雷切尔:我在想罗伯特·洛威尔和你的对照 。
米沃什:有那样一些我嫉妒洛威尔的时候 。 我会说:“啊 , 他是聪明的;他有了一次崩溃 , 人们将他带到了疗养院 , 在那里他可以平静地写作;但是当我经历一次危机我却必须正常运转 。 ”
本文图片
雷切尔:对你的一首诗《紧身胸衣的挂钩》你附注评价说:“在我帮她解紧身胸衣的挂钩时 , 我赋予了它一种哲学的意义 。 ”在你那样做时 , 你能够构想给行为赋予意义吗?
米沃什:有关我们的意识和行为这一确定的二元论的问题非常有趣 , 也许是一个狡猾的问题 。 我知道一些人满脑子都是文学 , 于是他们的每一行为 , 甚至私人信件的写作 , 都是在构造艺术世界的想法下完成的 。 我们也可以想象 , 在他们对他们的哲学意义的冥想中 , 其实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生理功能的实现 。 但是回到你的问题 , 我猜测如果我们真的沉浸在爱之中 , 我们是不会有这些想法的 。
【|米沃什:写作是一种持久不变的抗争】雷切尔:你能否设想 , 举例说 , 一个人考虑一种性关系 , 为了让另一个人更接近上帝?
米沃什:我看不到那种有意识的谋划 。
雷切尔:那么是无意识的谋划?
米沃什:对 。 我的远亲奥斯卡·米沃什 , 他是一位法国诗人 , 写了一本很有趣的小说《爱的启蒙》 , 出版于1910年 , 一个对漂亮情妇的爱的故事 , 发生于18世纪的威尼斯 。 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慢慢才认识到肉体的世俗之爱是通向爱上帝的途径 。
雷切尔:你写道:“当人们不再相信善与恶/只有美能呼唤和拯救他们/以便让他们学会明辨是非 。 ”没有艺术的美我们就无法认识真理吗?
米沃什:一个正教神学家塞尔奇·布尔加科夫(Sergius Bulgakov)经常说 , 艺术是未来的神学 。 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 我不太喜欢这种会被我叫做艺术的宗教的东西 。 在二十世纪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定不移地崇拜艺术的普遍倾向 。 艺术变成了宗教的替代品 , 我对此深感怀疑 。 但是 , 无疑这里存在着应被尊重的东西——撇除那些势利的、不太高贵的、甚至自私的动机 , 或者艺术家对他们艺术的自吹自擂——因为 , 在一个缺少确定性和价值观的稳定基础的世界上 , 人们本能地转向或许是灵感充溢的神圣的艺术 。
雷切尔:在你的诗《紧身胸衣的挂钩》中你放入并超越了何种时空?
米沃什:这首诗是关于二十世纪初的年轻女人们的 。 在散文评论中我运用了那个时代所谓的堕落文风:“你要白孔雀吗?——我会给你白孔雀(white peacocks)” 。 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 就是我们总是风格的囚徒 。 我以前说过我们创造形式 , 但是形式在变 , 因为人类世界在变化 。 如果我们看1919年以来的电影就会发现那时的女人和现在的女人是不一样的——甚至她们的身体也不同 , 因为时尚、风格和衣着 。 我描写的那些女人屈从于她们时代的风格 。 绘画和诗歌的各样风格也是如此 。 我们的问题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风格;我们认识不到它 。 一百年后我们的衣着、风尚 , 我们思维的方式就会被打量 , 也可能会被认为有点滑稽 。 在我的这些散文片段中有一种怀旧 , 有一种冲破形式和风格的中介而和人类 , 和这些早已香消玉殒的女性交流的渴望 。
- |数字藏品,为什么在年轻人中火了?
- 青州|穆里尼奥:我职业生涯这么传奇,你们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解雇我!
- 妙玉|妙玉人生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不是身陷淖泥中,而是被骗进贾府
- 亚马逊|跳槽须提供上家公司的工资流水,为什么很多公司这么干?
- |近体诗语法11:什么是按断式?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 hr|HR自己招的人,为什么还需要背景调查?
- |夜读|为什么洛可可风格取代了巴洛克风格成为新的流行?
- |两个人谈起未来的职业规划,需要注意什么?
- 国企|“理想男友”职业新鲜出炉,国企职员垫底,什么职业成“香饽饽”
- 张起灵|《盗墓笔记》守门十年,张起灵为什么不怕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