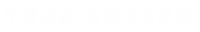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十 )
此外 , 方志也收录了各地修道院的基本信息 。 如威廉·兰巴德1576年出版的《肯特郡志》 , 就简要列举了肯特郡修道院的情况;威廉·布顿1622年出版的《莱斯特郡志》也涉及本郡修道院的内容 。 残缺的修道院建筑及其背后的各种传奇故事 , 自然激发古物学家无尽的思绪和历史沧桑感 。 威尔特郡古物学家及方志史家约翰·奥布里无限感慨地写道:“原来埋葬国王与显贵的教堂唱经楼 , 现在杂草丛生 。 ”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渊源 , 方志史家成为研究修道院史的重要力量 。 当然 , 方志所叙述的修道院 , 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 如有研究者指出:“威廉·布顿的研究未注意到修道院在中世纪经济与景观中的重要性 。 ”《沃里克郡古物》的作者威廉·达格代尔是英国修道院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 。 格雷厄姆·帕瑞认为:“在英国 , 威廉·达格代尔的修道院知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 ”威廉·达格代尔的《英格兰修道院史》详细记述了众多英国修道院的发展历史以及土地捐赠情况 , 并完整列出有关修道院的特许状 。 他以特许状为第一手史料 , 进行中世纪史的书写 , 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 , 在探讨修道院权力来源的基础上 , 阐述修道院的重要性 。 这是解散修道院运动之后 , 英国学界对修道院价值的重新思考 , 为后来的修道院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 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 1695年 , 托马斯·坦纳的《修道院记录簿》出版 , 成为修道院研究的总结性作品 。 他的弟弟约翰·坦纳解释道:“该书不是为了评论修道院的情况 , 或者为它的衰落悲哀 , 而是为了所有古物爱好者 , 给曾经在我们王国扮演重要角色的修道院一个概述与说明 。 ”
由此 , 在古物学家的努力建构下 , 修道院不再意味着无知与迷信 , 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 , 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 , 代表着虔诚与知识 , 宗教改革时期解散修道院对英国文化的传承是巨大损失 。 需要强调的是 , 这一时期古物学家对修道院的评价不涉及根本教义的分歧 , 毕竟新的时代是新教的时代 。
结论
古物研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考证与复原 , 古物学家更不是远离时代、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 。 有学者认为 , 古物学家不强调历史的政治功能 , 只是超然地求真 ,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 求真求实是这一时期古物学家共有的特征 , 实地考察、田野调查、查阅文献档案等 , 都体现了古物学家的研究风格 。 但是 , 古物学家不可能超然于自己的民族与时代 , 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 , 他们对民族认同的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
到17世纪末 , 不论是新教信仰 , 还是天主教信仰 , 甚至是流亡国外的古物学家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 即作为日耳曼人一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 具有坚毅的品质 , 充满活力与勇气 , 是一股复兴的力量 , 撒克逊因素(而不是不列颠人或者罗马因素)是英国族群的本质属性 。 正是在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 , 英国人才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他们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关系 。 在界定他们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时 , 他们以往侧重于封建关系或者是宗教因素 , 现在更关注族群属性 。 对于那些在族群属性和宗教信仰方面更为接近的人 , 英国人自然觉得更容易接纳 。 奈尔斯指出 , 这正是英国人接受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 , 以及后来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原因 。 因为这些所谓的外来者 , 都有着日耳曼人的血统 。 而那些与海峡对岸天主教法国关系密切的英国君主 , 自然就得不到英国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
在近代早期古物学家有关民族认同研究的基础上 , 19世纪的英国学术界正式形成了“撒克逊主义学派” , 代表人物是约翰·肯布尔与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 。 肯布尔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一书研究了盎格鲁—撒克逊先辈公共与政治生活所根植的原则 , 以及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机制 。 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童年时代的历史 , 也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成年时代的解释 。 古奇指出:肯布尔认为英国人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继承了最高贵的部分 , 现在的英国人与祖先之间保持了惊人的相似性;他的著作充满着日耳曼主义精神 。 19世纪 , 随着英帝国的形成 , 英美文化强势登场 。 “撒克逊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不再如其先辈那样小心谨慎地赞美撒克逊传统的纯洁性 , 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日耳曼精神以及日耳曼文化的优越性 。
- 英国|摘菜能赚55万?发达国家面临棘手问题,开始向全球撒钱抢人
- 奈特$英国最成功、最受欢迎的女性艺术家——皇家女爵士劳拉·奈特夫人
- 奥利弗&纯情与美丽~英国画家威廉·奥利弗女性人物油画作品欣赏
- 约瑟夫·吉卜林|被文坛严重排挤,英国诗人吉卜林十句格言,体现异样风情,收藏了
- 文化|英国创意与文化技能协会主席唐纳德·海斯洛普:艺术品市场需要在公共和私营领域之间创造更多平衡
- 巴特西发电站@英国巴特西发电站举行灯光秀 艺术装置美轮美奂
- 摩罗诗力说$英国人目击清朝刑场砍头,见到围观群众在欢呼,留下一句评价
- 展览|英国国家美术馆将展温斯洛·霍默:自然的静默与力量
- 塞缪尔·约翰生|新书架|《约翰生传》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盟主的脆弱与尊严
- 亨利·菲尔丁|亨利·菲尔丁笔下18世纪的英国:旧贵族统治下的世态炎凉与衰败